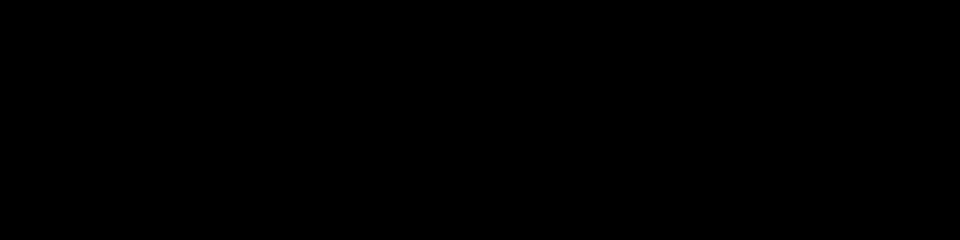
一個禮拜之前,昆山市一紙《關於對吳淞江趙屯(石浦)等3個斷面所屬流域工業企業實施全面停產的緊急通知》,在兩岸掀起軒然大波。在被要求全面停產的270家企業名單中,鴻海集團、台塑集團所屬企業赫然在列,被昆山市政府要求從2017年12月25日起至2018年1月10日期間全面停產,限制排放污水以改善水質。

因影響面過大,消息傳出當日昆山官方即連夜召開會議,決定暫緩實施停產決定。但政府對於環保問題之重視程度,亦可見一斑。巧合的是,就在12月25日當天,第693號國務院令《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出台,並於2018年1月1日起與《環境保護稅法》同步施行。
環保稅的開徵,是否意味著大批污染性企業將從此步入生死之劫?或者,因為各地對於環保稅的徵收標準不同而引起新一輪的企業遷徙?
稱生死劫過於言重,但新一輪的企業遷徙倒是完全可能。
作為首個明確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的獨立型環保稅稅種,環保稅的實質在於取代之前的排汙費,並同時建立“企業申報,稅務徵收,環保監測,信息共用”的多部門協作全新稅收征管模式,其根本目的在於強調環保而不在於稅,或者說,是用稅收的強制徵收甚至懲治手段,代替原來彈性空間較大的排汙費。
大陸對於排汙費的收取,源於2003年起施行的《排汙費徵收使用管理條例》。其中第七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按照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核定許可權對排汙者排放污染物的種類、數量進行核定。”按照“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由環保部門根據排汙費徵收標準和排汙者排放的污染物種類、數量,來確定排汙者應當繳納的排汙費數額。這種強制力不足的收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給予了環保部門較大自由裁量權的同時,也給了排汙企業可以尋租的空間。
從負擔上來講,環保稅的開徵雖然實行的是“稅負平移”原則,即基本上是在原排汙費基礎上轉化進行,但根據《環境保護稅法》第六條規定:“應稅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體適用稅額的確定和調整,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物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在本法所附《環境保護稅稅目稅額表》規定的稅額幅度內提出,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且同時,在2017年12月27日國務院印發的《關於環境保護稅收入歸屬問題的通知》中,明確環境保護稅為地方收入。

這也就意味著環保稅並非固定標準,而是以現行排汙費收費標準劃定的最低值,由各地政府自行確定各地稅額,並鼓勵地方上調收取標準,上限為最低標準的十倍,這就使得某些地區環保稅的開徵,會帶來比排汙費更高的生產成本。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不排除政府以犧牲環境換取地方經濟利益的可能,因而在環保稅額上作出較大讓步,從而引發新一輪的企業遷徙。
無論如何,自2016年底開始刮起的環保風,看起來不但沒有結束,實際上才剛剛開始。昆山本次270家企業被要求停產但又暫停實施的窘境,實際上也反應了地方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是地方政府GDP增長的業績要求與企業一旦停產可能面臨的巨額違約及社會穩定問題,另一方面則是還居民以青山綠水的生活品質的大勢所需。
在環保稅法剛開始實施的大背景下,大陸政府對於環境治理的決心和勇氣毋庸置疑。況且,政府決定並非兒戲,通知停產卻又暫停實施的情形,或可有一次、二次,但不可能發生第三次。對於眾多污染企業來說,要麼按規定繳納環保稅,要麼加大排汙整治力度以符合新的環保標準,要麼搬遷改造尋找其他適合生產地址,總之不可再存僥倖之心。
環保稅的具體內容,請參考貝斯哲2016年12月27日文章《新規速遞丨大陸環境保護稅一年後開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