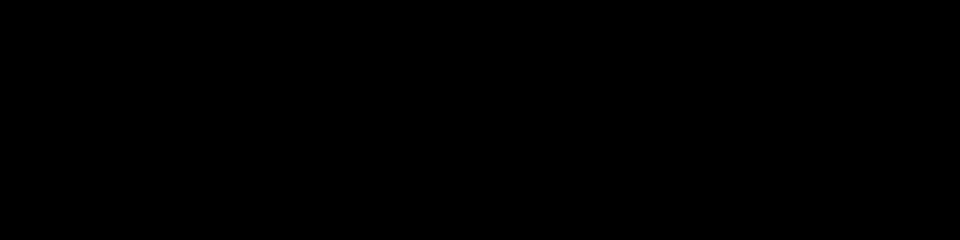
2017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并同时废止了自2014年5月实施至今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9号)(以下简称9号令)。
一部法规的出台,一定有其特有的时空背景和立法用意。众所周知,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大陆严控资金外流,尤其体现在境外投资的管控上,不仅在今年8月4日颁布有《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4号),12月19日又针对民营企业颁布了《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不难想象,新办法的出台,绝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对境外投资审核风向的乾坤扭转,而只能是在现有风格上的延续与深化。

果不其然。此次新办法虽然以“放、管、服”姿态推出了八项改革举措,比如,取消了程序上的项目信息报告制度、地方初审、转报环节和放宽投资主体履行核准、备案手续的最晚时间要求等,但体现在“管”上,则扩大了境外投资的解释范围,并强调事中与事后的监管,加强了惩戒措施。
因此,总体来看,新办法的出台,是用程序上的“放”,来平衡实质上的“收”,与这一年来的严控资金外流管理风格仍将一脉相承。
严控管理仍是“主调”
1、投资主体外延扩大
新办法第二条明确指出:“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以下称“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获得境外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投资活动。同时,第六十三条指出:境内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企业对境外开展投资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新办法以列举方式指出境外投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一) 获得境外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权益;
(二) 获得境外自然资源勘探、开发特许权等权益;
(三) 获得境外基础设施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
(四) 获得境外企业或资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
(五) 新建或改扩建境外固定资产;
(六) 新建境外企业或向既有境外企业增加投资;
(七) 新设或参股境外股权投资基金;
(八) 通过协议、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外企业或资产。
新办法直接将境内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再投资、境内自然人通过其控制境外企业对外投资统统纳入了管理体系,同时明确“控制”是指境内企业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拥有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或虽不拥有半数以上表决权,但能够支配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技术等重要事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新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境内自然人直接对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开展投资不适用本办法。这使得一直以来坊间期待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将有规定出台的传言,在本次新办法的实施中并未实现。
2、加强对擅自境外投资行为的威慑
新办法第三十三条强调投资主体未取得有效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的,外汇管理、海关等有关部门依法不予办理相关手续,金融企业依法不予办理相关资金结算和融资业务;以及第五十三条针对属于核准、备案管理范围的项目,投资主体未取得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而擅自实施的或应当履行核准、备案变更手续,但未经核准、备案机关同意而擅自实施变更的,由核准、备案机关责令投资主体中止或停止实施该项目并限期改正,对投资主体及有关责任人处以警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第二十六条关于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条件的禁止性规定来看,本次新办法强调“偷跑”项目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目的在于加强对擅自境外投资行为的威慑作用:一来威慑投资主体不得在境外从事威胁、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项目,二来不得违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严管违规逃汇、非法套汇等严重违反外汇管理、以及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3、境外投资敏感行业再次扩大
此次新办法虽在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敏感行业,包括:
(一) 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二)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
(三) 新闻传媒;
(四)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调控政策,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
敏感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相比9号令,新办法直接增加了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宏观调控政策限制行业。这里所指的宏观调控政策限制行业,当然也包括了〔2017〕74号文内明确列举的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和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

4、加强了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中与事后监管
9号令对于投资主体申请完成后的境外项目并不实施监管,而银行通常会对汇往境外的资金用途通过流水凭证等进行监管。但总体上,事后并无法切实监管资金用途以及境外项目实施过程。
而此次新办法用了较大篇幅构建了事中、事后监管体系,通过“重大不利情况报告”、“项目完成情况报告”、“重大事项主动问询和报告”、“信用记录联合惩戒”机制加以监督,要求投资主体主动对境外项目实施过程及不利于国家安全、资产损失等信息需通过网络系统报告;接受发改委的约谈函询。
针对恶意分拆、虚假申报、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擅自实施项目、不按规定办理变更、应报告而未报告、不正当竞争、威胁或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违规提供融资等违法违规行为,新办法提出建立境外投资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实施联合惩戒。这也代表着政府对境外投资项目持有的全程监管的态度,以及对“偷跑”、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等行为零容忍的态度。
简化审核才是“和声”
此次新办法的确也从各方面简化了投资主体申请核准、备案的流程,省去了一些“鸡肋”环节,试图增加实务操作效率。

1、取消了省级发改部门的转报环节
9号令对于“由国家发改委核准或备案的地方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均由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进行转报”,在实操中转报时间往往无法控制,以笔者近期处理的地方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核准申请的敏感类项目为例,由上海市发改委转报国家发改委核准,时长近2个多月。
而新办法在第十八条、十九条明确规定: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的,由其通过网络系统向核准/备案机关提交项目核准/备案表并附具有关文件,由其直接向核准机关或备案机关提交。与9号令相比,投资主体可直接在网上向国家发改部门申报,减少了中间环节和时间成本。
2、放款投资主体履行核准、备案手续的最晚时间要求
9号令规定的企业取得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的时间节点为“在对外签署具有最终法律约束效力的文件前”,此次新办法第三十二条直接改为“项目实施前”,这十分有利于企业合理安排交易及实际行政手续申请时间。
3、缩短了评估时间
从原则上不超过40个工作日改为原则上不超过30个工作日,这也防止境外投资核准/备案项目因为评估事宜而被整体拉长审核战线。
附:新旧办法主要修改对比表










